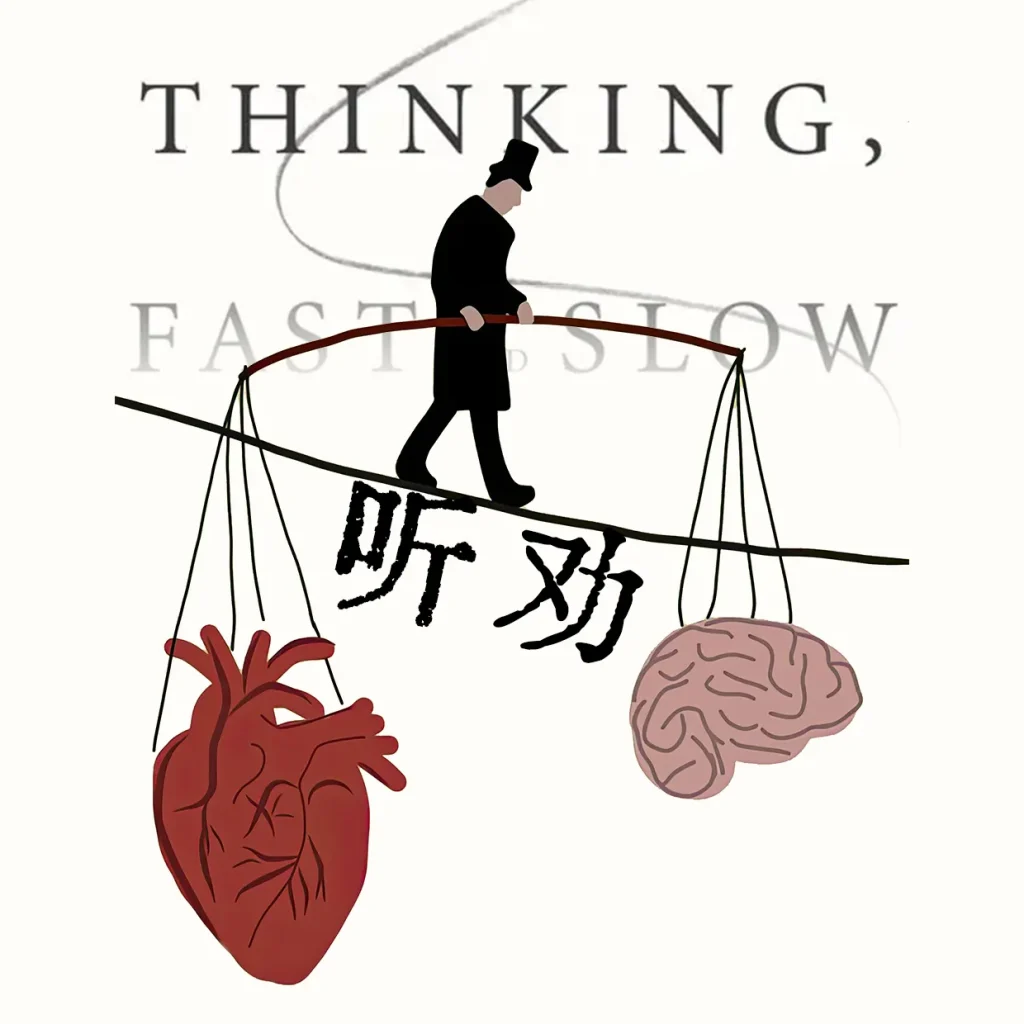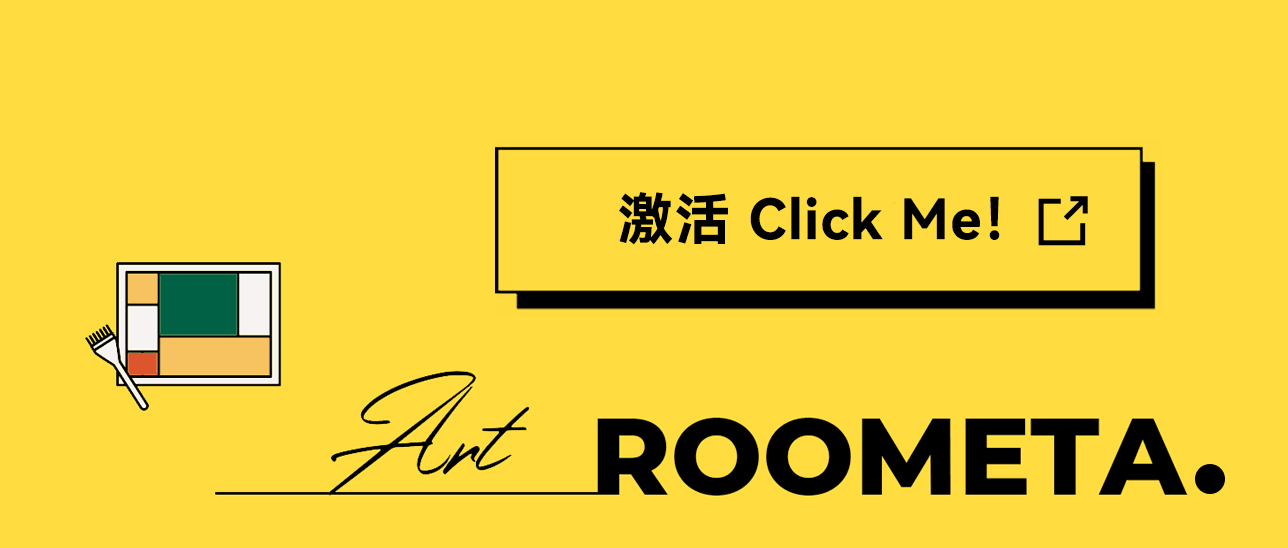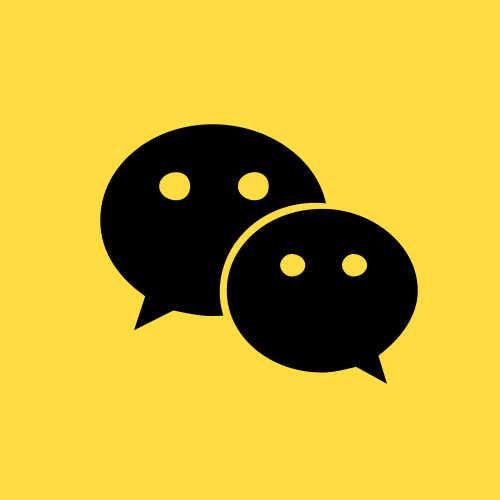梭罗植物学研究历程:
●早期学习(1828-1837):
– 在康科德学院首次接触植物学,师从菲尼亚斯·艾伦
– 在哈佛大学期间,植物学被包含在博物学课程中
●转折点(1846-1848):
– 1846年博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加入哈佛大学
– 1848年阿萨·格雷出版《植物学手册》,这成为梭罗系统研究植物的重要工具
●系统研究时期(1850年后):
– 1850年开始系统收集植物标本
– 开始详细记录植物开花日期和木本植物发叶时间
– 研读多位植物学大师的著作,包括米肖、塔克曼、劳登等
●研究特点:
– 逐渐从业余观察转向科学研究
– 经常使用拉丁语学名记录植物
– 在科学研究和诗性观察之间存在矛盾。
ROOMETA 室友计划线上文化社区
梭
罗不是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第一个研究植物的人。长他一辈的爱德华·贾维斯博士和查尔斯·贾维斯博士两兄弟(Drs. Edward and Charles Jarvis)曾在小镇收集了很多标本,那时梭罗还没从哈佛大学毕业。梭罗当然也不是这里最后一位植物研究者。他的文字激发了人们对康科德植物的兴趣,这种热情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从未间断过,今天仍在继续。可能新英格兰地区没有其他村镇的植物曾受到如此长久、不间断的关注。这块令人尊崇的土地,镶嵌着河流、肥美的草甸、湖泊、沼泽、石灰质悬崖,为植物学家奉献了无以匹敌的植物多样性(1 190个物种,应该还有更多),可能新英格兰地区同等面积的任何其他地区都无法与它媲美。
雷·安杰洛是被广泛认可的康科德历史植物群方面的领军权威学者。从1974年到1998年,他任职于位于马萨诸塞州贝德福德市的哈佛大学康科德野外工作站。1979年到1984年,他担任新英格兰植物俱乐部维管植物分会的助理负责人,1984年到2008年任该分会负责人。1990年至今任职于哈佛大学标本馆。安杰洛和戴维·布福德(David Boufford)博士合作的新英格兰地区植物地图集项目即将完成。他还是北美植物项目的地区评审人。2012年到2014年,安杰洛编辑了他对康科德植物的实地和学术研究成果,并在线发表了《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维管植物》(The Vascular Flora of Concord, Massachusetts),这是至今为止最全面的康科德植物史著作。他的相关出版物包括《哈佛的两封梭罗信件》(Two Thoreau Letters at Harvard)、《重新发现梭罗的攀缘蕨》(Thoreau’s Climbing Fern Rediscovered)、《康科德地区乔木和灌木》(Concord Area Trees and Shrubs)、《亨利·戴维·梭罗日记植物索引》(Botanical Index to the Journal of Henry David Thoreau)、《爱德华·S.霍尔揭秘》(Edward S. Hoar Revealed),以及《缅怀:理查德·杰弗森·伊顿》(In Memoriam: Richard Jefferson Eaton)。安杰洛记录192个康科德植物物种现状的文章《关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植物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物种灭绝的言论的评述》(Review of Claims of Species Loss in the Flora of Concord, Massachusetts, Attributed to Climate Change),发表于在线杂志《植物神经元》 (Phytoneuron)2014年总第84期1—48页。《植物学家梭罗》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1984年,同时出现在《梭罗季刊》 (Thoreau Quarterly)第15期和《亨利·戴维·梭罗日记植物索引》 (Botanical Index to the Journal of Henry David Thoreau)。植物学索引在线版见www.ray-a.com/ThoreauBotIdx/。
梭罗最初接触植物学这门科学的时间,要追溯到他在康科德学院上学期间(1828—1833)。植物学是该校开的科目之一,任课教师是菲尼亚斯·艾伦(Phineas Allen)。在同一时间,他还参加了康科德文化会馆的讲座,植物学是诸多讲座主题之一。梭罗在哈佛读书期间(1833—1837),学校没有开设植物学这门课,但是该学科内容包含在博物学下,著名昆虫学家撒迪厄斯·W.哈里斯(Thaddeus W. Harris)任教。大概是在这一时期,寄宿在梭罗家的普鲁登斯·沃德(Prudence Ward)同样对植物学感兴趣。梭罗后来回忆说(《梭罗日记》,1856年12月4日),这一时期他开始看雅克布·比奇洛的《波士顿植物集》(无疑是1824年第二版)。他主要是在找各种植物的俗名和生长地点索引。由于当时没有使用任何体系,他在这个阶段学到的拉丁学名很快就忘光了。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梭罗在家乡小镇教过一段时间书。博物学是他教授的科目之一。他和学生说,他非常熟悉当地花朵的开花时间,熟悉到只要看哪些花在开放,就能判断当时是几月。1842年他受到邀请为《日晷》 杂志评审由马萨诸塞联邦委托的一系列博物学报告。这一系列报告中有可敬的切斯特·杜威牧师(Rev. Chester Dewey)写的《马萨诸塞州草本植物报告》(Report on the Hervaceous Plants of Massachusells)。题为“马萨诸塞博物学”的所谓评审意见中,没有使用一个拉丁植物名称,也许是故意为之。梭罗的意见是,只把植物列出来(杜威的著作基本就是植物清单),不足以充分代表本州的植物资源。此时,就算梭罗想这么做,他植物学方面的科学知识也还不足以让他细致地评论该报告的技术水平。而且他也没有踏及马萨诸塞州足够多的地方,也就无从判断报告的完整性。
杂志评审由马萨诸塞联邦委托的一系列博物学报告。这一系列报告中有可敬的切斯特·杜威牧师(Rev. Chester Dewey)写的《马萨诸塞州草本植物报告》(Report on the Hervaceous Plants of Massachusells)。题为“马萨诸塞博物学”的所谓评审意见中,没有使用一个拉丁植物名称,也许是故意为之。梭罗的意见是,只把植物列出来(杜威的著作基本就是植物清单),不足以充分代表本州的植物资源。此时,就算梭罗想这么做,他植物学方面的科学知识也还不足以让他细致地评论该报告的技术水平。而且他也没有踏及马萨诸塞州足够多的地方,也就无从判断报告的完整性。
从留存至今的19世纪40年代的梭罗日记和信件来看,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时期他科学地从事过植物学研究。在1843年5月22日从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写给妹妹索菲亚的信中,他写道:“告诉沃德小姐,我会努力充分利用我的显微镜,如果发现了任何新的能制成标本的花,我会扔进我的摘记簿的。”梭罗首次使用植物的拉丁名称貌似是在《梭罗日记》里(普林斯顿版第2册第9页),1842年9月12日他提到了“Mikania scandens”,即攀缘假泽兰。同一段文字,略改动后的版本出现于1849年的《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A Week,普林斯顿版第44页)。
梭罗第一次在发表的著作中使用本土植物的科学名称,似乎是在1848年。在梭罗当年发表在《文学艺术联盟杂志》(Union Magazine of Literature and Art)上关于卡塔丁山的文章的最初版本里,出现了“pinus nigra”这个名称。这是比奇洛植物手册里用来称呼黑云杉(学名:Picea mariana)的名称。

黑云杉(学名:Picea mariana)
在这篇文章后来的版本里,梭罗把这一名称改为阿萨·格雷(Asa Gray)手册使用的名称,也就是“Abies nigra”,同时还插入了另一个拉丁名称“Vaccinium vitisidaea”,即蔓越橘。梭罗的古典语言背景和他对词源学的喜爱,自然地吸引他使用植物的拉丁(和希腊)语科学名称。
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两个事件,激发了梭罗对博物学分类的兴趣。第一个事件是1846年科学界“真正的巨人”的来访——博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接受了哈佛大学的一个职位。正如A.亨特·杜普雷 所指出的:“不仅是他的成就,还有他非凡的人格魅力,在本地科学家中引起了轰动。”就在第二年,在梭罗与阿加西斯的助手詹姆斯·艾略特·卡伯特(James Elliot Cabot)的往来信件里,他频繁使用科学名称讨论收集动物标本的事宜。
所指出的:“不仅是他的成就,还有他非凡的人格魅力,在本地科学家中引起了轰动。”就在第二年,在梭罗与阿加西斯的助手詹姆斯·艾略特·卡伯特(James Elliot Cabot)的往来信件里,他频繁使用科学名称讨论收集动物标本的事宜。
第二个事件更加直接地确立了梭罗对植物学的喜爱,那就是1848年阿萨·格雷出版了《植物学手册》 (Manual of Botany)第一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新英格兰的植物研究一直停留在相对初级的水平。这本书的出现,预示着这一萧条时期的结束。这个手册可以用来鉴别美国东北部的维管植物、苔藓和地钱,虽然和杜威的报告以及比奇洛的参考手册一样枯燥,但是更加全面、精确。
两年前,乔治·B.爱默生的《关于马萨诸塞森林中自然生长的乔木和灌木的报告》出版了。这一著作虽然涵盖的范围要小得多,但是比之前任何一个手册都更加关注每个物种的出现和用途,而且描述得更加细致。格雷手册和爱默生报告都使用了一种自然的分类体系来排列各个物种,没有像比奇洛一样采用卡尔·林奈(Carolus Linnaeus)的人为分类体系。这两册书不同于新英格兰之前任何一本植物学著作,它们的出版不可避免地激发梭罗更加系统化地研究植物。
这两个事件后,梭罗首个触及博物学的著作是《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1849年出版。从这本书开始,梭罗终于在他的自然著作中少量使用拉丁命名法,特别是在涉及鱼类时。他在书中甚至还提到了阿加西斯。但是梭罗使用植物的科学名称非常少——仅限于8种植物,它们都相对常见,容易辨识。

在1906版《梭罗日记》中,第一个本土植物拉丁名出现在1850年5月的一篇日记中——“Prunus depressa”(现在叫Prunus susquehanae,即沙樱)。从该年的8月31日开始,植物科学名称经常出现在《梭罗日记》的春、夏、秋篇目中。据梭罗后来回忆(《梭罗日记》,1856年12月4日),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用更科学的方法研究植物。在他系统化的标本收集簿里,最早的标本也同样来自1850年。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梭罗开始了一个高强度的项目,让自己熟识康科德的植物群。他读了一些大师的植物学著作,包括弗朗西斯·安德烈·米肖(François André Michaux)、爱德华·塔克曼(Edward Tuckerman)、约翰·劳登(John Loudon)、阿萨·格雷和卡尔·林奈。在《梭罗日记》中,他提到了林奈的人为植物分类方法与自然分类体系之间的对比,但总是评论说,两者都没有论及植物的诗性层面。当他寻找关于植物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科学著作时,得到的消息令他沮丧,博物学家、哈佛图书管理员撒迪厄斯·W.哈里斯告诉他,该门类所有的书他都已经读过了。
这些年勤奋的野外考察,让他抱怨观察过度了:
我有过度观察的习惯,以致感官得不到休息,承受持续工作的负担……当我发现自己总是低着头,双眼盯着野花时,我曾想过,作为纠正措施,也许可以养成观察云朵的习惯。但是不行!那项研究将会同样糟糕。(《梭罗日记》,1852年9月13日)
我觉得那么多的观察活动让我狼狈不堪……我几乎因此有点轻微的头痛。(《梭罗日记》,1853年5月13日)
1852年冬天,没有花可供观察了,他开始研究地衣。
梭罗既是艺术家,又是博物学家,不足为奇地,这两方面之间的矛盾开始浮现出来:“滋养了理解力,却剥夺了想象力,这是什么科学?”(《梭罗日记》,1851年12月25日)“我已开始对科学失望了。”(《给索菲亚·梭罗的信》,1852年7月13日)
1850年他的项目开始时,梭罗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特别是有关木本植物的,意识到这一点有点令人震惊。结束瓦尔登湖栖居生活已经3年了,梭罗还辨识不出本地春季最早开花的乔木白枫(《梭罗日记》,1852年5月1日);不知道生长在康科德的杉树只有一种,即黑云杉(《梭罗日记》,1857年5月25日);区分不出毒漆藤和毒漆树(《梭罗日记》,1851年5月25日);不认识桤叶荚蒾(《梭罗日记》,1851年9月11日)。梭罗后来这样回忆这种无知的状态:
我记得大约是在那些日子里,我饶有兴致地注视着沼泽,心里想,不知道我有朝一日对植物是否能熟悉到认识里面的每条枝、每片叶所属物种的程度,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认识见到的每种植物(除了草和隐花植物),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遇到的。虽然大多数花我都认识,任何一片沼泽里我不认识的灌木也不超过半打,但我还是感觉它像迷宫一般,里面藏着千种陌生的物种。我甚至想过要从一端开始,认真仔细地从头到尾翻一遍,直到我认识里面的全部。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两年后我就获得了这样的知识,还没费那番力气。(《梭罗日记》,1856年12月4日。)
19世纪50年代初期,梭罗萌发出记录植物开花日期和木本植物发叶时间的狂热念头。他描述了自己有时是如何费尽周章去探明某种野花的确切开花日期的——“奔走于小镇的各个方向,有时可能还会进入相邻的村镇,经常一天跑二三十英里路。”(《梭罗日记》,1856年12月4日)难怪他说:“要观察花瓣是怎样次第舒展开来的,你能做的只有尽力而已。”(《梭罗日记》,1852年6月15日)他对开花日期的痴迷从未减退过。发现哪个地方某种植物开花日期更早,就是一场胜利:“你可能需要花半生的时间,才能发现应该去哪儿找开得最早的花朵。”(《梭罗日记》,1856年4月2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梭罗以10年为跨度整理了植物开花以及其他物候性日期,填入精细的月度表格。他可能计划写一本书来描绘康科德典型的一年,这些代表了这本书的骨架。
随着梭罗植物学知识的快速增长,他担当起本镇植物学家的角色。对他而言,了解康科德稀有植物的生长地点,是非常重要的事。1851年11月,在进行土地勘测期间,他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出现了——攀缘蕨(即掌叶海金沙),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蕨类,在当地非常少见。1853年5月,他发现了艳丽的火焰草,并感叹道:“有些其实非常惹眼,可大多数勤劳的路人就是长时间看不见它……如果你没有在恰当的那一两周里碰巧拜访它们的生长地点……”在同一个月里,他在《梭罗日记》中讲述了从一位当地猎人嘴里套出粉红杜鹃藏身之处的趣事。“偏偏就在我自以为对花了解非常多时发生——猎人让我看到了他发现的紫杜鹃,或者叫粉红杜鹃。”(《梭罗日记》,1853年5月31日)这件事让他看到很深的寓意。他劝服猎人的部分论点是“我是植物学家,我理应知道”。
梭罗对康科德植物的兴趣,自然地扩展到他在家乡之外的旅途中。这几本著作记录了他最早期的重要旅行——《克特登与缅因森林》(Ktaadn and the Maine Woods,1848年)、《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加拿大的美国北佬》(An Excursion to Canada,1853年)——它们大多只提到常见植物,相对极少使用拉丁名称。《瓦尔登湖》也基本是这样。1854年10月,梭罗游历了马萨诸塞州沃楚西特山,体现在《梭罗日记》里的主要就是在那儿见到的乔木、灌木的一串俗名。这只是一个先导,为未来远足中更多、更长以拉丁语为主的清单做准备。例如,1856年9月,梭罗在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旅途中所收集的植物,被认真地罗列在《梭罗日记》中。类似的,《梭罗日记》中记录1855年7月鳕鱼角之行的文字里,充斥着那片海岸上特有花朵的拉丁名称。作为对比,他那年发表于《普特南杂志》(Putnam’s Magazine)上关于鳕鱼角的文章里,只出现了两个植物科学名称。
到了1857年,梭罗明显已经超越了雏鸟试飞的阶段,可能已经成为马萨诸塞州水平较高的业余植物学家之一。这一年,他写了旅行记录中最详细的植物清单之一——缅因州埃里盖什(Allegash)之旅。这一清单记录在《梭罗日记》里(但1906版没有包括这一部分),也是《缅因州森林》(1864年)的附录。这个清单也包括了他在1853年9月缅因州奇森库克(Chesuncook)之行中见到的物种。
1858年7月,梭罗做出了可能是他对新英格兰植物学界最重要的贡献。他攀登了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山——新英格兰第一高峰——并分区列出了该地区的植物名录,这是有史以来最详尽的名录,在20世纪前无人能出其右。一个月前,他列出了在新罕布什尔州莫纳德诺克山(Mt. Monadnock)发现的植物。1860年8月重游该地时,他为这个名录补充了更多植物笔记。这种分区的植物名录,可能是受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提出的植物垂直分异和水平分异之间关系的启发。
1861年开启明尼苏达之旅时,梭罗的植物学造诣已颇深,但他的健康状况在下滑。他热情饱满的旅伴小霍勒斯·曼(Horace Mann,Jr.)是位年轻的博物学家,在哈佛研究植物学,本该很有前途,可惜19世纪60年代就死于肺结核。梭罗在这次旅行使用的记录簿里大量使用了植物的科学名称——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还包括常规的旅途所见植物名录。这将基本是梭罗对植物学的最后涉猎了。
虽然梭罗在远足旅行中表现出浓厚的植物学好奇心,但康科德植物一直是他的心头最爱:“对我而言,这里的很多野草所代表的生命力,比加利福尼亚的大树还要丰富,前提是如果我哪一天拜访加利福尼亚的话。”(《梭罗日记》,1857年11月20日)1858年2月4日,梭罗惊讶地在康科德发现了拉布拉多茶(即宽叶杜香)。但是他一年半前就预见到了这一发现:“为什么这里不生长像伯克郡还有拉布拉多那么狂野的植物呢?……在拉布拉多野外,我也绝不会发现比康科德的一些角落更狂野的地方了。”(《梭罗日记》,1856年8月30日)
在宽叶杜香藏身的那片沼泽地,梭罗还发现那里的黑云杉上长着一些奇怪的东西。这里,他错过了描述一种当时学界未知植物的机会:当地罕见的寄生植物油杉矮槲寄生。
从1858年开始,梭罗开始认真地从事起禾草和莎草研究来。这两类植物对大多数现代植物学家来说都相对不熟悉。两三年里,他获得了关于康科德出现物种的大量知识。他的收藏包括该镇的近100个该类物种(是迄今在该镇发现此类物种的近二分之一)。其他发现和分类难度大的植物种类,比如地衣、苔藓和真菌,由于没有优秀的地区性指导手册,研究无法进行。结果,除了地衣,他极少从科学角度提及这些种类的植物。就算是地衣,他也远没有像了解维管植物那样,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在一篇名为“地衣学者梭罗”(Thoreau,the Linchenist)的短文中,地衣学家小雷金纳德·希伯·豪(Reginald Heber Howe Jr.)评论说,梭罗对地衣的观察记录表现出他“对物种知之甚少,没有任何技术性知识”。但是,作为在梭罗身后60年在康科德研究地衣的学者,豪指出,梭罗了解林林总总的形态类型,欣赏它们在大自然中所占的位置 。就算他收集过地衣、苔藓和真菌标本,也没有已知标本留存下来。
。就算他收集过地衣、苔藓和真菌标本,也没有已知标本留存下来。
在他那个年代,区域性植物学家相对较少,无人可供梭罗分享他的观察结果。新英格兰最有名气的植物学家是哈佛大学的阿萨·格雷,但很显然梭罗不容易接触到他,而且他的名声主要在于标本植物学领域,而不是野外植物学。格雷的传记作家A.亨特·杜普雷说,不管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还是梭罗,他们和阿萨·格雷都没有交集,他把这个归因于经验主义者格雷对超验主义的敌意。
除了阿萨·格雷,当时新英格兰的所有其他植物学家几乎都是业余的。在梭罗会面过的相关学者中,最博学的要数来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约翰·L.拉塞尔牧师(Rev. John L. Russell,1808—1873)。拉塞尔是一位论派 牧师,在马萨诸塞园艺学会做了40年植物学和植物生理学教授,后来还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认识很多描述植物新物种并以他们自己的名字命名新物种的人。拉塞尔对苔藓、地钱和地衣特别感兴趣。鉴于拉塞尔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胞弟查尔斯的哈佛同学,梭罗很可能是通过爱默生第一次听说拉塞尔的。拉塞尔于1838年9月拜访了爱默生,那时爱默生在他的《爱默生日记》中提到,他是“头脑里按因果顺序排列事物,而不是像商店或柜子那样排列事物的人”。
牧师,在马萨诸塞园艺学会做了40年植物学和植物生理学教授,后来还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认识很多描述植物新物种并以他们自己的名字命名新物种的人。拉塞尔对苔藓、地钱和地衣特别感兴趣。鉴于拉塞尔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胞弟查尔斯的哈佛同学,梭罗很可能是通过爱默生第一次听说拉塞尔的。拉塞尔于1838年9月拜访了爱默生,那时爱默生在他的《爱默生日记》中提到,他是“头脑里按因果顺序排列事物,而不是像商店或柜子那样排列事物的人”。
1854年8月,梭罗与拉塞尔在康科德第一次相遇,这可能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梭罗渴求着权威植物学鉴定,证据就在他带拉塞尔逛康科德那三天的笔记里。其间,他们拜访了攀缘蕨。拉塞尔于1856年7月23日第二次来访,来看一种小型黄色睡莲。1858年9月21日最后一次见面时,拉塞尔一定注意到了梭罗植物学知识的增长,至少他一定知道了梭罗对禾草和莎草的最新兴趣。那天,梭罗到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安角(Cape Ann)埃塞克斯研究院(the Essex Institute)拜访拉塞尔。那天的行程分为两部分,上午看研究院的收藏,下午去野外。梭罗抓住机会,确认了一些鉴别难度较大的植物,比如柳和地衣。
其他有著作发表的植物学家,包括哈佛大学药物学教授雅克布·比奇洛和乔治·B.爱默生,都生活在波士顿地区,但显然社交圈子相对较高,不可能结识梭罗。校长和植物学家爱默生是波士顿博物学会主席,而梭罗1850年被选为该学会通信会员(因为贡献了一只美国苍鹰)。根据A.亨特·杜普雷的说法,爱默生是波士顿科学团体的主任,1842年阿萨·格雷到哈佛任职就是通过他的努力达成的。虽然梭罗经常去看该学会的收藏品,拜访它的图书馆,但他对那里的兴趣主要在于动物。而且由于不是正式会员,他跟会员格雷、比奇洛和爱默生没有见面机会。结果是,梭罗与拉塞尔的会面,代表着他与专业级别植物学家的最亲密接触。
虽然严格地说,本杰明·马斯顿·沃森(Benjamin Marston Watson,1820—1896)是一名园艺学家,但他和梭罗之间的友谊让他们有了分享植物学笔记的重要机会。1845年,沃森在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建立了他的老殖民地苗圃(Old Colony Nurseries)。这个地方成了康科德超验主义者最爱去的地方。同年(在瓦尔登湖安居后仅一个月),梭罗转送给沃森一些康科德不常见的乔木和灌木的果实和种子,很明显,目的是为沃森的园艺事业提供帮助。沃森则把他苗圃里的一些罕见标本送给梭罗,雇他勘测他的农场,邀请他到普利茅斯做讲座。根据《梭罗日记》的记录,他经常到普利茅斯拜访沃森,在那儿他能看到新英格兰外来植物的活体植株。
梭罗和马斯顿·沃森的一位共同朋友叫乔治·P.布拉德福德(George P. Bradford,1807—1890),他是一名教师,有一段时间在普利茅斯和沃森一起做了一些商品蔬菜栽培,曾经参与过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的实验。他曾于1830年在普利茅斯一所女子学校里教授植物学。《梭罗日记》提及布拉德福德的地方很简短,主要讲的是稀有植物发现。有暗示似乎在说,布拉德福德在植物学方面也有超验主义情怀。梭罗记录了爱德华·霍尔的建议,送了一片攀缘蕨叶子给布拉德福德,“提醒他太阳依然照耀着美国”(《梭罗日记》,1854年8月14日)。奇怪的是,在梭罗已出版的书信中,关于布拉德福德只有一处不重要的提及。
在乔治·B.爱默生关于马萨诸塞乔木和灌木报告的前言里,他向布拉德福德、拉塞尔,以及纳提克(Natick)的奥斯汀·培根(Austin Bacon,1813—1893)致谢。这篇前言简直就是1846年马萨诸塞州植物学家名录了。奥斯汀·培根是一名土地测量员兼博物学家。1857年8月24日梭罗拜访了他。他带梭罗看了纳提克的很多植物观光胜地。梭罗对纳提克的兴趣,毫无疑问源自他读过的奥利弗·N.培根(Oliver N. Bacon)所著的《纳提克历史》(History of Natick),书中有一份罕见植物名录(《梭罗日记》,1856年1月19日)。
康科德居民中,梭罗能与之以任何深度讨论植物学的,只有爱德华·S.霍尔、迈诺特·普拉特和他妹妹索菲亚。爱德华·S.霍尔是一名退休律师,曾和梭罗一道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White Mountains)、缅因州的阿拉加什河和佩诺布斯科特河。1844年梭罗意外点燃了康科德费尔黑文树林,霍尔也在场。与梭罗一样,霍尔收集并制作植物标本。说真的,霍尔的收藏品质量远远更高,特别是就收藏资料的可辨识性和细节而言。他的标本大部分是在1857—1860年采集的,其中包含了很多禾草和莎草。同样是在这几年,梭罗也在研究这些鉴别难度系数很高的植物科属。奇怪的是,《梭罗日记》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一起研究过。《梭罗日记》提到霍尔的篇章,表明霍尔让梭罗注意到了他发现的各种植物珍品。很明显,他对博物学,特别是对植物多样性的热情,使他成为梭罗北上旅行中上佳的旅伴。
迈诺特·普拉特是一名农场主兼园艺学家,在布鲁克农场尝试着干了四年后,移居到康科德。如果说有任何人和梭罗一样熟悉康科德野花的话,那个人就是迈诺特·普拉特。显然他也同样独立搞研究,因为在《梭罗日记》中梭罗对他的提及,只限于两人间少量的沟通,内容有关康科德稀有物种的生长地点。曾有三次,普拉特带梭罗参观了森林里属于他的地盘——庞卡塔赛特山(Punkatasset Hill)和埃斯塔布鲁克树林(Estabrook Woods)(《梭罗日记》,1856年8月17日、1857年5月18日、1857年6月7日)。就植物学而言,这两个地方属于该镇最富有的地带。普拉特后来做的一件事,让他在后世植物学家中享有一定的声誉,那就是把外来植物移入康科德。梭罗很少做这样的事,但是学名为Nasturtitium officinale的豆瓣菜是他引入的外来植物之一(《梭罗日记》,1859年4月26日)。
从康科德免费公立图书馆里的植物标本室来看,索菲亚·梭罗(1819—1876)对植物学的兴趣与她哥哥相比科学性相差甚远,但审美方面胜出很多。她制作的植物标本里,很多一页中含有几个标本,摆放得赏心悦目,但很少有信息记录它们的名称或生长地点。梭罗提到,在她妹妹的植物收藏室里有三种花他从来没在康科德见过,分别是轮叶朱兰、红果延龄草、穿茎垂铃儿(《梭罗日记》,1852年9月22日)。这些都是当地罕见物种。奇怪的是,没有证据表明,梭罗在康科德境内(索菲亚发现它们的地方)见过其中任何一种。这也许表示兄妹俩在竞争。
在梭罗那个时代,新英格兰地区的植物学家总体很少,这无疑是因为当时基本上没有带插图的指导手册或通俗的实地指南讲述这一地区的植物群。这类书19世纪晚些时候才面世。梭罗间接地抱怨过这种匮乏(与英国相比较):“几页描绘植物不同部分的图片,附上植物学名称,比用文字解释几箩筐更有价值。”(《梭罗日记》,1852年2月17日)他发现他能找到的植物描述都不尽如人意,“大多数植物学家对不同物种的描述,都让我很有意见,比如说柳树……不重点说明该物种的独有特征,需要非常仔细地查看和对比,才能在描述中找到不同之处”(《梭罗日记》,1853年5月23日),“你没法通过科学描述来准确地鉴定一种植物,长期实践后才能做到”(《写给B. B.怀利的信》,1857年4月26日)。
梭罗的藏书(1957年沃尔特·哈丁整理)反映出当时植物学参考书相对匮乏。他拥有几乎所有跟康科德维管植物相关的书籍,还有一些略沾边的。沃尔特·哈丁列出的书目包括以下植物学著作:
 这个书单应该再加上雅各布·比奇洛的《波士顿植物集》的各个版本。梭罗在他的日记中经常提到它,这样看来他手里一定有这本书。梭罗不时查看的三部指南分别是埃莫斯·伊顿(Amos Eaton)的《北方和中部各州植物学手册》(A Manual of Botany for the Northern and Middle States,各个版本)、约翰·托里的《美国北部和中部植物》(Flora of the Northern and Middle Se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26年出版)、托里和格雷的《北美植物》(Flora of North America,1838—1943年出版)。这些书能提供的信息,没有超出比奇洛和格雷手册很多。托里和格雷的著作是三者中最详细的,但是不完整,而且涵盖的地理范围太大,使用起来不方便。如果梭罗手头有现代野外指南和植物手册,他的专业知识会增长得更早、更快。他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令人称奇了。
这个书单应该再加上雅各布·比奇洛的《波士顿植物集》的各个版本。梭罗在他的日记中经常提到它,这样看来他手里一定有这本书。梭罗不时查看的三部指南分别是埃莫斯·伊顿(Amos Eaton)的《北方和中部各州植物学手册》(A Manual of Botany for the Northern and Middle States,各个版本)、约翰·托里的《美国北部和中部植物》(Flora of the Northern and Middle Se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26年出版)、托里和格雷的《北美植物》(Flora of North America,1838—1943年出版)。这些书能提供的信息,没有超出比奇洛和格雷手册很多。托里和格雷的著作是三者中最详细的,但是不完整,而且涵盖的地理范围太大,使用起来不方便。如果梭罗手头有现代野外指南和植物手册,他的专业知识会增长得更早、更快。他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令人称奇了。一家植物鉴定准确的标本馆,是最好的全天候植物学参考书。遗憾的是,在梭罗生活的时代,地区性标本馆同样还处于襁褓之中。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藏品很多,梭罗仍然没有放过参观的机会,包括波士顿博物学会(《梭罗日记》,1856年7月19日),还有埃塞克斯研究院(《梭罗日记》,1858年9月21日)。但是,最好的收藏品在个人手中,是私人收藏。
梭罗自己的标本室(标本数量最后有900多个),无疑是当时马萨诸塞州东部规模较大的标本室之一。梭罗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写给玛丽·布朗(Mary Brown)的一封信中(1858年4月23日),他评论说:“很愿意带你参观我的标本室,藏品很多。”从现代视角来看,他为这些收藏记录的数据总体来说很差。大约一半的标本只记录了植物名称,忽略了最重要的信息——采集地点。这大大减损了收藏的科学价值。涉及麻烦的种类,比如禾草、莎草和柳树时,他提供的数据总体要比其他藏品好很多,但是往往很难解读(快速或随意写下,用的是铅笔,字还很小)。他用草帽装植物从野外带回家的习惯,往往导致他采集的多是小型、不合格或不完整的样本。
按照日期标注最早的标本来判断,梭罗明显是在1850年左右开始有组织地采集标本的(相对于在普通书本或手册里随便收藏而言)。也是在同一时期,他开始使用更科学的方法研究植物学。显然,梭罗创建标本收藏室,是为了帮助自己鉴别在康科德以及旅途中发现的植物,而不是将其作为在未来植物学家中名留青史的手段(这是建立私人标本室的一个常见意图)。
梭罗去世后,他的标本收藏是这样处理的:按照他的遗愿,约100个禾草和莎草标本被赠给了他的植物学研究伙伴爱德华·霍尔,其余部分(约800个标本)赠予波士顿博物学会。归霍尔所有的梭罗标本随同霍尔自己收藏中的大部分,最后由霍尔的女儿M. L. B.布拉德福德夫人于1912年赠予新英格兰植物学俱乐部。这家俱乐部的标本室目前已转移到哈佛大学。梭罗的标本被仔细地放置到标准尺寸的标本台纸上,附有标签,包括梭罗用铅笔书写的采集数据,还有霍尔的誊写版本。在被收入俱乐部藏库前,他们为这些标本编制了目录,并制作了影印资料。从科学角度讲,这是梭罗标本收藏里最有用的部分,因为它们附有采集数据,所涉及的植物种类研究难度大,而且还有后来的植物学专家,比如M. L.弗纳尔德(M. L. Fernald)为之添加的注释。
梭罗标本收藏中的大部分留在了波士顿博物学会,直到1880年后者将其转给康科德公立免费图书馆。1959年,该馆又把收藏交给了哈佛大学格雷标本馆。梭罗的标本现在还在那里,与该馆其他收藏品分隔开单独存放。跟梭罗的禾草和莎草标本不同,这部分收藏的状况,大多看上去和梭罗去世时差不多。由于相对很难被看到,科学价值也没那么高,后世植物学家对它们的评论性关注极少。这些标本用几条胶布不怎么牢固地粘贴到大开本薄台纸上,偶尔会用小尺寸纸。通常每张台纸不止容纳一个标本,有时会有六个或更多,同一页上经常还容纳了不止一个物种。一般来说,梭罗只在标本附近用铅笔写了该物种的拉丁名称。有时有采集地点数据,比如“特鲁罗市’55”(Truro’55)、“伯瑞特波罗”(Brattleboro)、“缅因’57”(Maine’57),用铅笔标注在对应标本的旁边,或是写在一片纸上,插到标本下面。台纸用铅笔标注了编号,并根据格雷《植物学手册》第二版的要求,以系统化顺序排列。收藏分为六部分,每部分都分别保存在一个破旧的大尺寸硬纸板夹里。波士顿博物学会整理了一个物种列表,收录在一个单独的册子里。
与他妹妹的私人标本室相比,梭罗的收藏更有组织性,标本在台纸上的陈列方式是由实用性决定的,而不是出于审美需要。尽管工作人员的操作有时有点欠谨慎,疏忽也是有的,但从整体来讲,这些标本目前状况良好。令人惊讶的是,标本几乎没有遭受昆虫破坏。有几件标本还保留着足够亮丽的原生色泽,仿佛是去年刚刚制作的一般。这些收藏很脆弱,这让它们还有可能在不熟悉如何正确处理标本的人手里继续遭受无心的摧残。
梭罗在有生之年只发表了一篇与植物界有关的作品,那就是《森林树木的更迭》(The Succession of Forest Trees),这篇文章整理自1860年9月他在康科德的米得尔塞克斯农业学会(Middlesex Agricultural Society)的发言,次月发表于《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和区域性农业报告中。实至名归地,这篇论文被视作对生态学的贡献,而不是对植物学的贡献。即便如此,这可能也是他最重要的科学论著(与其说是原创观点,不如说是对各种观点的原创性发展和表达)。
梭罗的文章《秋色》(Autumnal Tints)和《野苹果》(Wild Apples)整理自《梭罗日记》,最初作为演说稿面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修改了这两篇文章。在他死后,这两篇文章于1862年发表于《亚特兰大月刊》(Atlantic Monthly)。梭罗认为植物学文献中存在空白,这些文章是他为填补这一空白所做的部分努力。当他开始认真研究植物时,他试图找到“更加具体、通俗的著作,或者某些侧重书写野花的传记……因为我相信,每一种花都有很多热爱者,都曾有人忠实地描述过它们”(《梭罗日记》,1852年2月6日)。《秋色》和《野苹果》是对植物的审美欣赏。虽然立足于科学,但是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文学作品的典范。
在梭罗留下的零碎手稿里,有些好像是他正在写的成系列的文章,标题包括“野果”(Wild Fruit)、“种子的传播”(The Dispersion of Seeds)、“叶落”(The Fall of the Leaf)和“新英格兰本地果实”(New England Native Fruits)。从这些手稿中,利奥·斯托勒(Leo Stoller)整理后串起了一篇名为“越橘”(Huckleberries)的文章,其文风和内容非常像《秋色》和《野苹果》。该文的关键词是“我赞美的浆果”(“我赞美”的原文“which I celebrate”是梭罗的原话),它表达了这几篇文章的主旨精神。
梭罗研究植物,但并没有对植物学做出重要贡献。他最重要的植物学成就,只能得到大多数新英格兰植物学家的勉强承认——他首次详细描述了新英格兰第一高峰华盛顿山的植被带。虽然这一描述直到他死后很多年才得以发表,但他的观察的确提供了一个对照点,让后世植物学家发现了新英格兰最有趣的植物所在地中的高山植物的变化。
梭罗对康科德植物的大量研究,还成为后世了解该地植物变化的参照。梭罗植物研究的重要性在这里,而不在于为康科德带来特别的植物学发现。他在康科德的植物观察和标本采集,可能是至那个年代为止,新英格兰最完整的镇区植物调查。从本质上讲,梭罗为后来的植物学家提供了19世纪50年代康科德植物群的“照片”。康科德没有任何其他人,像梭罗在那十年里那样深入地研究植物。他的植物鉴定能力很强(过了最初的青涩阶段之后),他有疑惑或犯错的地方都是连专业植物学家(以及他们的手册)也会存疑之处。梭罗对康科德不常见植物的生长地点极其熟悉,这方面只有迈诺特·普拉特能与之媲美。梭罗的植物学知识面非常广(包括禾草、莎草和地衣),在这方面,只有爱德华·霍尔和刚去世不久的理查德·J.伊顿能望其项背。
梭罗的目的不是为他那个时代的植物学知识库添砖加瓦。相反,他研究植物是想更加清晰地辨识大自然为他的家乡披裹的衣裳的质地,当然还有他的新英格兰,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这块布料的一部分:“我对我周围同时生存着的每一种植物都感兴趣——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了植株较大的那些。它们是我的邻居,与我共同居住在地球的这个角落,而它们的名字我也耳熟能详。”(《梭罗日记》,1857年6月5日)他对被驯化的植物兴趣极小,几乎丝毫不感兴趣:“我对家庭中的植物从来都提不起一丝兴趣。”(《梭罗日记》,1856年12月4日)他早期对花的关注与超验主义对大自然的总体观点是一致的——把大自然视作灵感的源泉,看作可以获得教益的有生命的课堂,它是在邀请你去亲身体验,而不是给你机会去分析。后期他用系统方法研究植物时,内心存在哲学的不适,随后他又对其加以合理化:“我曾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现在我是她的观察者。”(《梭罗日记》,1852年4月2日)“人们研究科学书籍,只是为了学习博物学家的语言——为了能够与他们交流。”(《梭罗日记》,1853年3月23日)直到最后,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博物学家或植物学家,而是作家,这是他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年,学习这些田野的语言,以便能更好地表达自己。”(《梭罗日记》,1857年11月20日)但是,就一名作家而言,这样完全、自觉地了解家乡的植物,是史无前例的。这让人不禁去遐想,他这样勤勉地研究植物,是想要酝酿出什么样的伟大著作呢?
雷·安杰洛
Source:A Kind of Timeless Jazz Masterpiece – The AtlanticJames Kaplan
Related 相关影像拓展阅读
Related 相关影像说明文
Related 相关影像拓展阅读
ROOMETA 室友计划线上文化社区
Editor’s Pick 编辑推荐
Editor’s Pick 编辑推荐
写出来,能治愈一颗破碎的心吗?
了解一个作家最直接的方式,不是读他的作品,而是窥探他的日记。日记是一个过于私密的东西,即便卡夫卡、伍尔夫等作家们并不想出版自己的日记,最后这些私密的文字却在删减之后,得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作家的日记,会在违背逝者意愿的情况下出版呢?
阅读全文Kind of Blue: 迈尔斯·戴维斯如何打造史上最伟大的爵士乐专辑
《Kind of Blue》是迈尔斯·戴维斯于1959年发行的经典爵士专辑,其录音质量和音乐创作受到高度赞誉。专辑的音调问题在后续版本中得到修正,评论界普遍认为其为戴维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尽管专辑取得了成功,戴维斯在随后的生活中经历了警察暴力事件,对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1964年才重新找回创作激情。
阅读全文